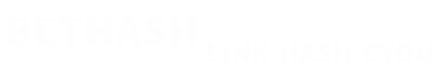
HASHKFK
BETHASH官方网站(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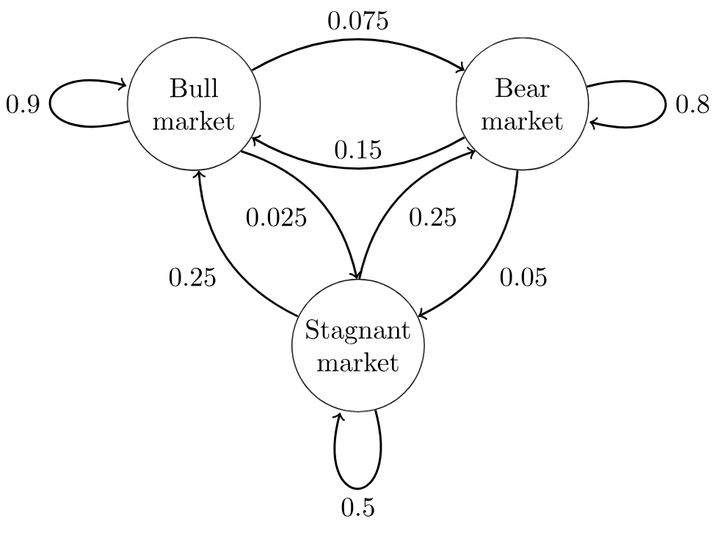
在哈佛大学这样的顶级学术圣地,女学生因穿得“太女性”而被教授直呼为“斯通小姐”;男学生可以加入导师的社交俱乐部接受指导,女学生被拒之门外,甚至在毕业时被导师明言“从未给女人颁发过博士学位”;女性教授被逼离开自己热爱的领域……我们通常熟悉的第二代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模样,经常出现在托德·海因斯那些关于五六十年代美国郊区中产的电影画面里,她们要么从事办公室打字员的工作,要么成为精致、得体的中产主妇,毕竟“如果你1960年从大学毕业,你还是会穿着围裙、高跟鞋和裙子出现在厨房里,你得待在家里,不会出去工作”。
2017年10月,《》和《纽约客》报道数十名女性声称数十年来遭到米拉麦克斯影业和韦恩斯坦电影公司联合创办人、电影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性侵。#Me too标签开始在社交媒体发酵。2020年5月,《哈佛深红报》报道,该校人类学系三名教授被指控性侵犯。被指控的三名教授分别是:前系主任西奥多·贝斯特(Theodore C.Bestor),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日本;约翰·科马洛夫(John Comaroff),主要研究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以及盖里·尤尔顿(Gary Urton),主要对前哥伦布时期进行研究。
可当我们交谈时,她坚持要我理解她在哈佛大学的经历并非一无是处——接替威利成为她导师的初级教师杰里·萨布洛夫,就是她了不起的伯乐。她还想让我知道,哈佛大学的歧视不足为奇;相比她在职业生涯中即将面临的情况而言,那“只能算是一次热身罢了”。比如在她现在担任荣誉教授的佛罗里达州,她系里的一位年长男性总对她区别对待,会在办公室前台对她“大发脾气”。这个教授成为系主任之后,他毫不掩饰对男同事们的偏袒,比如只给他们涨工资。玛丽提出了申诉,要求重新考虑自己的工资(几年里她多次提交过申诉)。由行政部门选定的一名大学女教师审查了她的案子,并驳回了她的申诉。当玛丽来到她办公室讨论裁决结果时,对方告诉她,“你的工资的确不公平,但生活本身就不公平”。
伊丽莎白·斯通,就是那位因为被误导而放弃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资助的学生,于1971年来到考古系。她被这里的氛围吓到了。多年以后,她称哈佛大学是“我去过的性别歧视最严重的地方”。为了弱化性别,系里的其他女生都穿得“很中性”。伊丽莎白拒绝这么做,结果她成了班上唯一不被教授直呼其名的学生。她成了“斯通小姐”。当伊丽莎白和芝加哥大学商议要尽快离开哈佛大学时,她跑去和秘书们道别,这群秘书也都是女性。其中有个人祝贺她:“你们中终于有人逃离这里了!”
1981年,当莎莉·福克·摩尔(Sally Falk Moore)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拿到终身教职时,她是系里唯一拥有终身教职的女性,也是整个哈佛大学文理学院16位女性终身教授之一。摩尔教授感觉自己仿佛孤身一人立于寒风中,系里接纳她,是把她当成朋友,在决策上却并没有拿她当回事。行政部门提升她为研究生院的院长、本科生宿舍马瑟楼(Mather House)的主管,她觉得自己被利用了。行政部门的想法是希望尽可能让女性被看见,以此来提升女性在大学的地位。但这些行政工作消耗了她的时间,反而让她在人类学系的管理上更加没有了发言权。
2014年,拉德克利夫校友聚会,南希·霍普金斯的演讲进行到最后,她告诉听众,学术界的性别歧视最终成了不可争辩的事实。她1994年就发现,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院中仅有8%的教职工是女性。而在哈佛大学,这个比例是5%。歧视最终被量化了。她将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给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结果发现“麻省理工学院的女老师们都心知肚明,但每个人都不敢说出口。在精英教育的体制下,如果你说自己被歧视了,大家只会觉得是你不够优秀”。
2005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拉里·萨莫斯(Larry Summers)在一个关于多样性与科学的会议上说,因为与生俱来的生理差异,男性在数学和科学相关的职业中比女性表现得更出色。听到这里,南希·霍普金斯径直走出了房间。萨莫斯虽然承认社会化的作用,但还是淡化了它的重要性。即便他说的话在事后引起了轩然,他仍向《波士顿环球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行为遗传学的研究表明,人们之前归因于社会化的事情根本不是由社会化引起的。”根据《卫报》的报道,在拉里·萨莫斯任校长的头三年半时间里,提供给女性的终身教职数量从36%下降到了13%。2006年6月,萨莫斯卸任;下个学期,我来到了哈佛大学。
伊瓦·休斯顿并不是一个人。萨蒂·韦伯,几年前和我一起上卡尔的课的那个梳辫子的女孩,同样把简的故事当作一种警示。她在斯坦福大学的讲师、理查德·梅多以前的一个学生之所以告诉她这个故事,也是为了提醒她注意卡尔。而萨蒂和伊瓦一样,都把简的故事看成系里性别互动关系这个大背景的一部分。在哈佛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内,她不假思索地告诉我,她的看法是,“这算是一种比喻⋯⋯恃强凌弱的老教授们利用他们的学术地位,让[他们指导的学生]非但不能说不,还可能渴望从中获得兴奋感”。
我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名单。科拉·杜波依斯是社会人类学系的,不是考古系。辛西娅·埃尔文-威廉姆斯(Cynthia Irwin-Williams)是怀俄明州地狱峡Hell Gap,位于美国怀俄明州东部大平原的一处考古遗址,包含大量史前古印第安人和太古时期的文物,对北美考古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考察的负责人之一,为哈佛大学培养了不少最优秀的考古学家,但她从未获得终身教职。鲁斯·特林汉姆也是。塔蒂阿娜·普罗斯古利亚可夫,就是那个随身携带烟灰缸的玛雅学者,在系里连正式的职位都没有。
萨蒂对她的论述做了限定。从来都没有,除了有一回,有人短暂地获得过终身教职。诺琳·图罗斯(Noreen Tuross)教授在系里待了五年。2009年,人类进化生物学系从人类学系分出来之后,她转去了这个系。萨蒂有印象,诺琳是被解雇的。(我和诺琳聊的时候,她说加入人类进化生物学系是她自己的选择,但在她的理想世界里,她本可以继续待在人类学系的。“分系的时候我的确提过申请,同时在两个系任教,但被人类学系驳回了。原因你得去问他们。我不清楚。”)
性骚扰和性侵犯的经历可能也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2014年发布的第一份关于野外考察时遭受性骚扰及性侵犯的系统性调研,接受调研的500名女性中有70%曾受到性骚扰,140名男性中有40%曾受到性骚扰。超过四分之一的女性曾遭受性侵。大多数男性是被他们的同伴骚扰或性侵,而大多数女性则是被她们的上级骚扰或侵犯。另一项调查表明,相比被同辈骚扰,由上级实施的性侵及性骚扰造成的心理创伤更严重,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更大。
我渐渐开始看到我在本科时没有能力认识到的事:即便一个体制中的个体都是好人,他们所构成的这个体制也依然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正因为我和系里所有这些女谈,研究她们形态各异的不幸,我才开始意识到体制的惯性有多大的腐蚀作用。另一方面,理查德和莎莉是人类学系的教授。让我颇感惊讶的是,尽管人类学家的职业生涯聚焦于观察人类的行为模式,但一旦轮到观察自己,他们却并不一定比我们做得更好。正如伊瓦·休斯顿曾经告诉我的那样,“要承认你属于你研究的那个世界,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