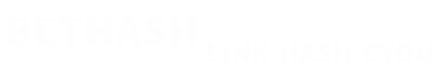
HASHKFK
BETHASH官方网站(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克孜尔石窟是中国所有石窟壁画中,被揭取最严重的一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东方在沉暮中徘徊,一众踏着黄沙而来的西方探险者开启了一场文明的流失。中国壁画中最出色的代表——寺观、石窟壁画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斯坦因、伯希和、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奥登堡、大谷光瑞等人深入河西走廊远至新疆,文物商贩卢芹斋等人活跃于中原。于是,精美的中国壁画如同一部被撕碎的史诗——新疆壁画多流落于欧洲和日本,山西壁画飘零美国和加拿大。
那场“丝绸之路大美术展”,中国并没有参加,展厅中却陈列着大量精美的中国壁画,尤其那几幅出自克孜尔石窟的珍品,深深刺痛了他。那时,他还没有去过克孜尔石窟,没有想到,与克孜尔石窟壁画原作的初见,竟是在异国他乡。那一刻,他站在别国的土地上,越是细看,越是心痛。王岩松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如果不出国,这些原本属于中国的壁画,我们都没有机会见到。”这让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便现在无法追回这些遗珍,但如果能用自己的技艺临摹复制出来,让国人欣赏到这些壁画,不也令人欣慰吗?何不把流失国外的这些壁画,“画”回故土?由此,王岩松开始四处奔走搜集资料,临摹流失海外的壁画。
赵莉每天抢时间拍照、建档,哪怕是指甲盖大一点的文物,也捧在手心拍摄,每天在18度恒温恒湿的库房里工作得大汗淋漓。她为库房里的新疆文物系统地建立了卡片档案,查出了很多博物馆原档案中存在的差错,也帮助博物馆解决了不少疑问。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非常认可赵莉的工作,但因为拍摄雕塑时需要搬动文物,博物馆时任亚洲部主任和赵莉有些分歧,好在当时的馆长鲁克思非常理解她的特殊情结。“面对着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就好像是我们家丢失的孩子,这些宝贝丢失100年了,好不容易找到它,我必须得把家底摸清楚。”赵莉说。
将散落世界的壁画“归位”,比搜集资料更为艰难。当年德国探险队将壁画揭取后,为了方便携带,把壁画切成了小块,到了柏林以后再把它们拼接起来,结果拼错了很多,有些把不同洞窟的壁画拼接在一起,还有些居然和其他风格相似的石窟壁画混在一起,分辨极其困难。还有许多壁画边缘严重损毁,有些碎成小碎块,难以衔接。曾有人说她这项工作像拼图游戏,赵莉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这绝非拼图那样简单:拼图中相邻两块的图案颜色衔接自然连续,拼接后更是严丝合缝,无须应对文物本体的复杂损耗与信息缺失。”
“我不是把图像存放在电脑里,而是将洞窟结构与壁画细节铭刻在大脑中。每当发现某幅壁画可能与某个洞窟相关,大脑便会自动建立链接,给壁画归位。”赵莉这样形容她的工作。壁画复原的过程恰似刑侦破案,容不得半点疏漏,需细究每一处蛛丝马迹 —— 既要逐帧核对图像内容的衔接吻合度,也要精准校验尺寸比例的适配性。有时即便完成复原,搁置一两日后再复盘,一旦发现细节偏差,便只能毫不犹豫推倒重来。而对于那些尚未明确原位的壁画残片,她更是无时无刻不在脑海中反复推演、琢磨其归属,力求还原历史原貌。
天已经黑了,江苏理工学院传统壁画研究所的工作室里,王岩松仍在作画。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他一直在研究、临摹中国传统壁画尤其是流失海外的部分。尽管由于工作原因,王岩松可以零距离贴近国内壁画,但搜集流失国外的壁画信息则颇费心力。“好在国外博物馆允许拍照。”王岩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国外博物馆,他常常一大早进馆,“看着这些海外珍迹会忘了饥饿”。当然,除了亲摄,他也借助同行共享的资料、学者提供的文献,以及网络数据库。对不同来源的材料,他都会仔细比对、深入研究。
这两铺《平阳府朝元图》现为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原址古建筑早已不复存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山中商会将这些壁画切割制成六幅卷轴画,将干硬的泥地仗换成了柔软的棉布撑托,这件作品先运到日本,后又辗转到了纽约,再从纽约倒卖到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经多次修缮,留存至今。画中朝元的主要神祇和部属被描摹得栩栩如生,堪称元代壁画艺术的巅峰。熟悉壁画者或觉其与芮城永乐宫三清殿壁画《朝元图》颇为相似,王岩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两者一脉相承,而永乐宫壁画完成的时间比这铺要晚,虽同属民间绘画系统,却带有更强的官方背景,也许出资人地位更高、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多,规模更为宏伟,并采用沥粉贴金,等级更高。
当然,有些壁画的流失有其复杂的原因。王岩松在复制《药师经变图》时了解到,在广胜寺下寺后院东厢房廊檐下存民国18年(1929年)所刻《重修广胜下寺佛庙记》碑,碑文记载了卖壁画的经过:“1928年,广胜寺濒临坍塌,僧人不得已出售壁画《药师经变图》予古董商,筹款修寺,否则寺毁画亡,实属无奈。”其中,《药师经变图》被纽约收藏家赛克勒收购,1964年,捐献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修复后永久性地陈列在以赛克勒命名的大厅里。广胜下寺后殿南西壁的《菩萨伏案图》于1950年由卢芹斋捐赠给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藏。而如今,广胜寺除水神庙存有元代壁画外,其余仅余切割痕迹与零星残片。
如今,山西寺观壁画大量流失在北美,而新疆壁画多被西域考察队或盗宝队带去了欧洲和日本。其中,一些已损毁、不复存世的壁画,在王岩松手里得以“重生”,例如本属于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誓愿图》。《誓愿图》15幅,展现释迦牟尼前世与过去佛的十五次相遇,并被预言未来成佛的场景。20世纪初,柏孜克里克石窟被德国探险者勒柯克严重破坏,他将《誓愿图》揭取运到柏林,之后毁于二战战火。二战爆发前,勒柯克曾在1913年出版大型画册《高昌》,王岩松根据画册将已经毁去的壁画《誓愿图》复原了出来,“只为给后人留下一点残存的记忆”。
每当临摹古代壁画,王岩松常忆起昔日在山西幽静寺庙中的时光——阳光斜照,满壁斑斓,仿佛能触摸到古代匠师作画时的虔诚。为还原传统壁画的气息与神韵,他运用原材料、原工艺、原尺寸复制壁画。在江苏复制壁画,专程从山西运土;为防开裂,在泥中掺入麻刀与沙子;颜料与调色,亦遵循古法。甚至连墙体变化导致的剥落、变色等细微痕迹,他都一一描摹,力求形貌逼近原作。有些壁画不足半平方米,却需临摹一两个月。“我要做的,是收敛艺术创作的欲望与个性,尽显古人之韵。”王岩松说。
对赵莉而言,壁画的数字归位不仅是视觉层面的精准复原,更实现了流散四方的图像信息重归原位。依托这些复原后的壁画,诸多此前悬而未决的题材得以明确考证,而题材背后蕴含的佛教思想,亦清晰勾勒出克孜尔石窟当年盛行的佛教派别。为破解龟兹石窟群中诸多未解之谜,在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工作告一段落后,赵莉计划将研究延伸至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的壁画复原领域。文物保护与学术探索之路从无止境,正如她时常感念的屈原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